ЁЖЪХ Love and Death in ShanghaiЁЗЃЈ2007ЃЉ
РњЪЗМЭТМЦЌ ЗЂБэгкЃК2020-3-6 16:04|ВщПД:2124|ЦРТл:0|зжЬх:аЁ жа Дѓ ЗБЬх
ЁЖЪХ Love and Death in ShanghaiЁЗ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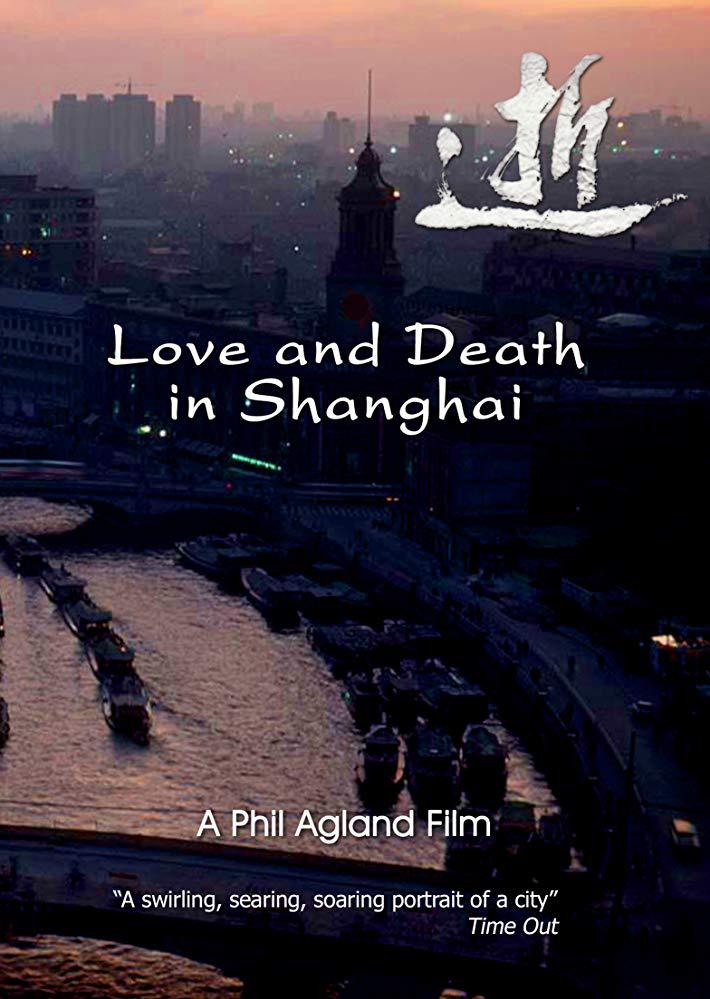
ЪХ Love and Death in Shanghai (2007)
ЕМбн: Phil Agland
РраЭ: МЭТМЦЌ
жЦЦЌЙњМв/ЕиЧј: гЂЙњ
гябд: гЂгя / ЦеЭЈЛА
ЩЯгГШеЦк: 2007-12-10
ЦЌГЄ: 100min
гжУћ: ЪХЁЊЁЊЩЯКЃЖЌвЙЕФАЎгыЫР
IMDbСДНг: tt1178579
1997ФъЪЧвЛИіЬиЪтЕФФъЗнЁЃИФИяПЊЗХЕФзмЩшМЦЪІаЁЦНЭЌжОШЅЪРЁЃЖјЩЯКЃЃЌзїЮЊвЛИіЙњМЪДѓЖМЪаЃЌе§ОРњзХОоДѓЕФБфЧЈЁЃетБфЧЈМШгаОпЯѓЕФЃЌШчГЧЪаОЩЧјИФдьЃЛвВгаГщЯѓЕФЁЂаФРэВуУцЕФБфИяЁЊЁЊБШШчШЫУЧЕФадЙлФюЁЂжаФъФаХЎЖдгкЛщвіКЭЩњУќЕФЗДЫМЕШЕШЁЃгЂЙњЕМбнPhil AglandХФЩуЕФЁЖЪХЁЊЁЊЩЯКЃЖЌвЙЕФАЎгыЫРЁЗзМШЗЕизЅзЁетИіГЧЪадОЖЏЕФТіВЋЃЌНЛЬцНВЪіСЫетзљГЧЪаРяМИИіШЫИїздВЛЭЌЕФЙЪЪТЁЃЫћбЁШЁЕФШЫЮягыЙЪЪТВЛЕЋНдгыАЎКЭЫРЯрЙиСЊЃЌЖјЧвЕчгАЪМжеБЃГжзХЧЁЕНКУДІЕФНкзрИаЁЊЁЊДгЙЪЪТЕФЦЬГТЁЂбнНјЕНИпГБМДНЋЕНРДЧАвЛЩВФЧСюШЫЦСЯЂЕФеХСІЃЌЮоВЛЯдЪОСЫЕМбнзПдНЕФПижЦФмСІЁЃдкЕчгАРыНсЮВдМШ§ЪЎЗжжгЕФЪБКђЃЌИїЬѕЯпЫїЭЌЪБЕНДяСЫв§ЖјВЛЗЂЕФБпдЕЁЊЁЊОгзЁгкЦЖРЇОЩЮнЕФКЂзгМДНЋОРњвЛГЁИпЗчЯеЕФаФдрЪжЪѕЃЛОЉОчаЁбндБвЛИідТжЎКѓТэЩЯвЊЕЧЬЈЙЋбнЃЛХЊЬУРяЕФЙбИОвЊУцСйдйЛщЕФОёдёЃЛЖјЩБКІХЎгбЕФЭХЮЏИЩВПМДНЋНгЪмзюжеЕФЩѓХаЁЃетСюШЋЦЌздЪМжСжеБЃГжзХвЛжжМЭТМЦЌРяВЛГЃгаЕФОчСвЕФаќФюИаЁЃ
ЭХЮЏИЩВПЩБКІХЎгбЕФЙЪЪТдкЕчгАжаеМОнСЫзюДѓЕФБШжиЁЃАЎгыЫРдкетИіЙЪЪТжаНЛжЏдквЛЦ№ЁЃвЛИіЙњМвЛњЙиЕФжЊЪЖЗжзгЃЌЖдздМКЕФХЎХѓгбКЮвдЯТДЫЖОЪжЃПаджЪИќЮЊбЯжиЕФЪЧЃЌЫћдкЩБШЫжЎКѓНЋХЎгбЕФЪЌЬхЗжГЩКУМИВПЗжЃЌХзШыНжаЁЃЪжЖЮжЎВаШЬЃЌСюШЫФбвдЯыЯѓЁЃЕчгАжвЪЕЕизЗЫцСЫДЫАИДгЩѓбЖЁЂаћХаЁЂЩЯЫпЕНжеЩѓЕФШЋЙ§ГЬЃЌЩБШЫЗИДгзюГѕЕФЕжРЕЕНзюКѓРсСїТњУцЃЌЪмКІепМвЪєдкХдЬ§ЯЏМфЕФБэЧщЃЌЮовЛВЛЯдЯжСЫШЫадЕФгФЮЂжЎДІЃЌСюЙлжкЩюЪме№ЖЏЁЃЖјЪмКІепМвЪєЖдгкЁАЩБШЫЗИвВЛсЫРЃЌЫћЕФМвШЫвВЛсФбЙ§ЁБЕФЫЕЗЈжЎОчСвХъЛїЃЌИќНЋЙЪЪТЭЦГіИќЩюЕФЁЂЕРЕТЗДЫМЕФВуУцЁЃ
КмФбЯыЯѓЁЖЪХЁЗГіздвЛИігЂЙњЕМбнжЎЪжЃЌвђЮЊШЋЦЌЕФЩЯКЃЗчЮЖЪЧДЫХЈжиЃЌНжЗЛСкРяКЭЩБШЫзяЗИНдВйвЛПкЯЪЛюЕФЩЯКЃЛАЃЌЫПКСУЛгаОчЧщЦЌЕФНУЪЮЃЌдЩњЬЌЕФгФФЌБШБШНдЪЧЁЃвђДЫЃЌетВЛНіЪЧвЛВППЩвдСюЮїЗНШЫИќзМШЗШЋУцЕиСЫНтЩЯКЃЕФМЭТМЦЌЃЌЖјЧвИќЪЪКЯЩЯКЃЙлжкЙлПДЃЌвђЮЊдкФЧаЉДЪВЛДявтЕФгЂЮФзжФЛБГКѓЃЌгаПЩвдСюШЫЛђЛсаФвЛаІЛђХѕИЙДѓаІЕФЖдЛАЃЌЖјаІЙ§жЎКѓЃЌЪЧЖдЩэДІЦфжаЕФЙЪЯчИќЩювЛВуЕФСЫНтЃЌИќОпЪЁЫМвтЮЖЕФзджЊЁЃ

ЭјгбЦРТлЃКЖМЪаТўгЮепЕФАЎгыЫР
ШчКЮВХФмСЫНтвЛзљГЧЪаЃП
ЪЧДгФІЬьДѓЯУЛђИќИпЕФЕиЗНИЉюЋЃПЛЙЪЧдкНжЕРжаЩЂВНгЮзпЃП
етСНИіНиШЛВЛЭЌЕФД№АИЗжБ№ДњБэСЫСНЮЛЁАЖМЪаЫМЯыМвЁБЕФЙлЕуКЭЗНЗЈЁЃЧАепЪЧНќФъвђжиЖСЁЖзЪБОТлЁЗдйЖШзпКьЕФХњХаЕиРэбЇМвДѓЮРЁЄЙўЮЌЃЌЫћШЯЮЊМйЪЙЙлВьепЕФЪгЕуВЛЙЛИпЃЌОЭВЛзувдПДЧхЁАзЪБОЁБетжЇОоЪжЖдГЧЪаПеМфЕФВйХЊЁЃКѓепдђЪЧвджјгаЁЖШеГЃЩњЛюЪЕМљЁЗЮХУћЕФЗЈЙњЫМЯыМвУзаЊЖћЁЄЕТЁЄШќЭаЃЌЫћШДЫЕжЛгаЁАТўВНепЁБЖјВЛЪЧЁАЙлВьепЁБВХФмСЫНтГЧЪаЕФецУцФПЃЌФЫжСгкГЧЪаБОЩэБугЩТўВНепЕФНХВНЪщаДЖјГЩЁЃ
ЧвВЛТлШЁОЖКЮепЃЌдкЫћУЧЕФЧАБВКЭЕМЪІКрРћЁЄСаьГЗќЖћФЧРяЃЌСНЬѕТЗЯпОЭЖМвбОБЛЕБГЩживЊЕФПЮЬтЃКвЛЗНУцЃЌвЊбаОППеМфКЭЩчЛсЕФЁАзмЬхЁБЃЌАбТфдкЭМжНЩЯЕФГщЯѓРЖЭМФвРЈЕНЫќЫљУЛгаПМТЧЕНЕФЮЪЬтгђжаЃЛСэвЛЗНУцЃЌФФХТШеШежиИДЕФвЛИіВЛЦ№блЕФЖЏзїЛђзЫЪЦЃЌЖМПЩФмдЬКЌСЫЮДБЛНвЪОЕФЕРРэЃЌЫљвдвЊНјааЁАШеГЃЩњЛюХњХаЁБЁЃ
етУДПДРДЃЌМЭТМЦЌЁЖЪХЁЊЁЊЩЯКЃЖЌвЙЕФАЎгыЫРЁЗПжХТецЕФУўЕНСЫСЫНтвЛзљЖМЪаЕФОїЧЯЃЌЛђаэвВОЭФмЙЛНтЪЭЃЌЮЊЪВУДЖШЙ§СЫЙлгАЭъБЯЕФЁАЯЭепЪБМфЁБКѓЃЌНЙТЧЛсВЛЖЯгПРДЃКВЛАВЁЂапРЂгжОЊВяЃЌвЛИіЭтЙњШЫЃЌОПОЙЦОЪВУДЛсБШМИЪЎФъФЫжСвЛБВзгОгзЁдкетзљГЧЪаЕФШЫЃЌИќзМШЗЕиДЅМАЕНСЫетзљГЧЪаЕФФкКЫЃП
ЮФУїгыЙцбЕЃЌзяЖёгыГЭЗЃ
гАЦЌПЊГЁАзЕЅЕЖжБШыЕибгајЕМбнЗЦЖћЁЄАЂИёРМЕТЩужЦжаЙњЙЪЪТЕФКѓ89а№ЪТЃЌНЋЬиЖЈРњЪЗЪТМўЮДдјдЖШЅЕФгрВЈЃЌКЭБЫЪБЕФЁАПЊЗХЁБМАСьЕМШЫУќдЫДЎСЊдквЛЦ№ЁЃдквьГЃНєеХЕФааЖЏКЭЗеЮЇРяЃЌОЕЭЗЖдзМСЫФЯЦжДѓЧХЁЂЭтЬВНЈжўШКЁЂЖЋЗНУїжщКЭНЈжўЙЄЕиЃЌЫцКѓИЉюЋзХИДаЫжаЕФГЧЪаЁЊЁЊдкетвЛЪгНЧЯТв§ГіСЫвЛЬѕжїЯпЃКвЛУћЧрФъХЎНЬЪІвЩЫЦБЛФагбГТе§ЛЊЩБКІЁЃ
АЂИёРМЕТМИКѕзЗзйСЫАИМўДгеьВщЕНжДааХаОіЕФЙ§ГЬЁЃДгЗЂЯжЪЌЬхЕФЯжГЁЁЂОЏГЕКѓзљЁЂЩѓбЖЪвЁЂЭЅЩѓЃЌвЛжБХФЕНХаОіКѓГТе§ЛЊБЛШЫвЊЧѓОЁПьаДКУвХЪщЃЌвдМАГТЕФЭЌЪТКЭЪмКІепЕФМвГЄЁЃШЋЦЌзюСюШЫгЁЯѓЩюПЬЕФЕиЗНФЊЙ§гкаЬОЏ803ЩѓбЖФЧЖЮЃЌаЬОЏСЌБЌДжПкЃЌЯХЕУЪмЩѓепдкРЯЪЕНЛДњЧАЬсСЫвЛИівЊЧѓЃКЁА㑚в ДђЮвЁБЁЃЁЊЁЊетецЪЕЕУв§ШЫЗЂаІЃЌБЯОЙдк20ФъЖрКѓЕФНёЬьЃЌЖдДЫЧщаЮКСВЛекбкЕиНјаагАЯёМЭТММИКѕЪЧВЛПЩФмЃЌИќВЛвЊЫЕгЩвЛУћЭтЙњШЫРДеЦОЕЃЁгШЦфЪЧ2008ФъОРњСЫЁАФуВЛИјЮввЛИіЫЕЗЈЃЌЮвОЭИјФувЛИіЫЕЗЈЁБЪТМўКѓЃЌВйзХДжПкЁЂДжБЩЕФЪаОЎааЮЊЃЌБиаыБЛИєОјдке§вхЧвзЈвЕЕФжДЗЈепаЮЯѓжЎЭтЃЌОЭЯёЁЖбВТпЯжГЁЪЕТМЁЗЫљеЙЯжИјЮвУЧЕФФЧбљЁЃФЧУДЃЌгЂЙњШЫЗЦЖћЁЄАЂИёРМЕТОПОЙЪЧдѕУДзіЕНЕФФиЃП
етИіЮЪЬтПЩФмБШЯыЯѓжаКУЛиД№ЃЌЩѕжСД№АИФудчвбВТЕНЃКЮоЗЧЪЧЁАЭЈКУСЫЙиЯЕЁБЁЃвђЮЊИќдчжЎЧАдкдЦФЯРіНХФЩуМЭТМЦЌЕФОРњЃЌАЂИёРМЕТНсЪЖСЫЙЋАВЕФИпВуВЂдјдкББОЉгаЙ§НЛЭљЃЌОнЫЕЕБЪБвЛЮЛПЊУїЕФДѓСьЕМЮЊЦфдкЩЯКЃЕФХФЩуПЊСЫТЬЕЦЃЌвтЭМНшДЫЦѕЛњШУ803зпЩЯЙњМЪЮшЬЈЁЃАЂИёРМЕТЦОетИіФбЕУЕФЛњЛсдкЩЯКЃвЛХФОЭЪЧ3ФъЃЌзюКѓжЦГЩГЄДя7аЁЪБЕФЕчЪгМЭТМЦЌЁЖShanghai ViceЁЗЃЈвЛвыЁЖЩЯКЃЗчдЦЁЗЃЉЃЌЙЫУћЫМвхЃЌзяЖёЪЧЦфжїЬтжЎвЛЃЌЁЖЪХЁЗдђЪЧгЩЧАепХЈЫѕМєМЖјГЩЕФЁЃЁЖЪХЁЗгЩвЛЬѕНЛДэЕЋЧхЮњЕФЯпЫїЧЃв§ЃЌМДЁААЎКЭЫРЁБЁЊЁЊМШгазяЗИЕФАЎКЭЫРЃЌвВгааЁЪаУёЕФАЎКЭЫРЃЌЩѕжСЪЧетзљГЧЪаЕФАЎКЭЫРЃЌШчДЫЃЌвЛЬзГЌГЄЕФЕчЪгМЭТМЦЌвЁЩэвЛБфГЩвЛВПГіЩЋЕФМЭТМЦЌЕчгАЁЃ
ЕЋЪТЧщгждЖУЛФЧУДМђЕЅЁЃМДБуЕМбнЪМжеМсГжЭЖзЂЪ§ФъЪБМфШкШыЕБЕиЩњЛюЃЌЕНЩЯКЃКѓЕФХФЩуВЂУЛгавђЮЊФУЕНИпВуаэПЩЖјвЛЗЋЗчЫГЃЌЕМбндјЭИТЖЃЌЁАМИКѕЫљгаОЏЗНЕФгАЯёЖМЪЧдкзюКѓАыФъжаХФЩуЕФЁБЃЌдкДЫжЎЧАЕФ2ФъМфЃЌЫћвЛжБдкгыЕБЕижДЗЈепжма§ЁЃЫфШЛдкРіНД§СЫЪ§ФъЃЌПЩжаЙњЕФЯчДхКЭГЧЪаШдгаУїЯдЕФВювьЃЌЖдАЂИёРМЕТЖјбдЃЌзяАИдђЪЧвЛжжИЉюЋФГДІЕФЧаШыЕуЃКЙцбЕгыГЭЗЃФмЬхЯжвЛИіЕиЗНЕФЮФУїГЬЖШЁЃгАЦЌНгНќНсЮВЕФвЛзРЗЙОжЩЯОЭЬсЕНЃЌ1997ПЊЪМЪЉааСЫОЕквЛДЮаоЖЉЕФЁЖаЬЫпЗЈЁЗЃЌЦфжадіМгСЫБЛИцШЫЮЏЭаБчЛЄТЩЪІЕФШЈРћЯИдђЁЃДгзювЛАуЕФвтвхЩЯЖјбдЃЌеЦЮеШЈСІЕФГЧЪаЙмРэепгІЕБЖдИіЬхЕФЛљБОШЈРћгшвдз№жиЁЃНЈдьГЧЪаЃЌвВЪЧЩшСЂвЛЬзаТЕФЙцдђЃЌгкЪЧЗИзягыжДЗЈвВЯѓеїзХЁАЧАГЧЪаЁБЕФЛьТвгыГЧЪаЛЏжШађжЎМфЕФВјЖЗЁЃдкДЫЃЌОЕЭЗЭЈЙ§зюМЋЖЫЕФЪТМўЃЌКЭЯнШыетИіЪТМўЕФШЫУЧЃЌРДЙлВьетзљЖЏЕДВЛАВЕФГЧЪаЁЃ
ЪаОЎЕФаоДЧбЇ
ЁАВЛАВЁБЪЧЖдФЧИіЪБЦкЕФзмРЈЃЌ1997ФъЕФЩЯКЃе§ДІгквЛИіЗЂеЙЕФЙиМќЕуЃЌГ§СЫЦЌжаУїШЗЩцМАЕНЕФВ№ЧЈЁЂДѓЫСПЊЗЂЁЂСїЖЏШЫПкгПШыГЧЪаЕШЮЪЬтЃЌЪЕМЪЩЯАЂИёРМЕТЗЧГЃЧхГўЩЯКЃдкЕБЪБЫљгіЕНЕФЩчЛсЮЪЬтКЭзДЬЌЃЌБШШчЯТИкГБЁЂЯТКЃГБЁЂГДЙЩШШЕШЕШЁЃвЛЗНУцЪЧвђЮЊЫћЙлВьЕУЙЛЖрЃЌСэвЛЗНУцЫћзїЮЊвЛИіЭтРДепДјзХРДздХЗжоЕФЖМЪаЛЏОбщЁЃ20ЪРМЭ70ФъДњЦ№ЃЌгЂЙњЗЂЩњСЫбЯжиЕФГЧЪаЫЅЭЫКЭГЧЪаЪеЫѕЯжЯѓЃКжааФШЫПкЯђНМЧјЧЈвЦЃЌГЧЪаЕФОМУНсЙЙЕїећЕМжТДѓСПЙЄШЫЪЇвЕЁЃДЫКѓЃЌеўИЎКЭУёМфВЛЕУВЛЭЖШыДѓСІЦјЭЦНјЁАГЧЪаИќаТЁБдЫЖЏЁЃАЂИёРМЕТЫЦКѕдкПёьЭЛНјЕФЩЯКЃПДЕНСЫгЂЙњЖМЪаЕФгАзгЁЃ
ПЩЪЧЃЌгАЦЌЖдетаЉЮЪЬтжЛвЛБЪДјЙ§ЃЌАЂИёРМЕТУЛгаДђЫуДгФГИіжЦИпЕуРДЩѓЪгетзљГЧЪаЕФЪаУёЩчЛсЁЃдкБЛЛвіВС§ежЕФГЧЪажаЃЌвЛжЛОЊЦцЕФблОІЃЌВЛНіМмдкЕФСЂНЛЧХЩЯЁЂНЈжўЙЄЕиРяЁЂЫежнКгХдЁЂЬсРКЧХМргќЭтЃЌЛЙМмдкСЫХЊЬУПкКЭдчЗЙЬЏЁЂЗЙЕъКЭЮшЬќЁЂЕиЬњКЭЙЋдАЁЂВЁЗПКЭзЩбЏеяЫљЃЌДШЩЦЛљН№ЛсКЭОЉОчАрЕФбЕСЗЗПЃЌЩѕжСМмНјСЫФЯЪаЧјЕФМИЛЇШЫМвЕФЮнРяЯсЁЃ
СїСЌЕФЩугАЛњВЛНіДјзХаазпЕФзЫЪЦЃЌЩѕжСЛЙГЩЮЊетаЉГЁЫљЕФвЛВПЗжЁЊЁЊдкБЛХФЩуепСГЩЯЃЌКмФбДЇЖШЫћУЧЖрДѓГЬЖШЩЯвтЪЖЕНСЫОЕЭЗЕФДцдкЃЌвжЛђЖрДѓГЬЖШЩЯЖдЦфЪгЖјВЛМћЁЃгаЦРТлЫЕАЂИёРМЕТЕФжаЙњгАЯёЪЧЁАfly-on-the-wallЁБЪНЕФЃЌЩугАЛњОЭЯёЖЄдкЧНЩЯЕФВдгЌЃЌЖјЫќЖдзМЕФШЫУЧздЙЫздЕиМЬајзХШеГЃЩњЛюЁЃетжжЩужЦЗчИёЃЌЖдгАЯёПеМфМИКѕБэДяСЫЭЌвЛжжвўгїЃКМДЪЙУцЖдСшМнгкздЩэЭтЕФвьжЪШЈСІЃЈЩугАЛњ/ЙњМвЧПСІЃЉЃЌШЫУЧЕФШеГЃЩњЛюЛЙЪЧЛсМЬајЃЌИіЬхзмЕУЯыАьЗЈЩњЛюЯТШЅЁЃЖдгІзХЪБДњИќЕќЁЂРњЪЗГЕТждйДЮЗЙіЕФНєеХЪБПЬЃЌШеГЃЩњЛюЪМжедкНжЭЗЯяЮВжаЭЌжїШЈШЈСІЕФМЏжаЙмПиНјаагЮЯЗЁЃ
ЩугАЛњИњХФСЫ4ЖдШЫЮяЃЌКУСкОгКУцЂУУТэАЂвЬКЭЭѕАЂвЬЃЌаФдрЯШЬьЛМВЁЕФаЁЗЖКЭФИЧзЃЌЗПЖЋЗыАЂвЬКЭЗППЭаЁЬЦЃЌЫяЪІИЕКЭЫћЕФЙиУХЭНЕмаЁМђЁЃетМИЖдШЫЮяжЎМфЛЅЯрЛЙгаНЛМЏЃЌКЭГТе§ЛЊЕФЙЪЪТВЛЭЌЃЌШеГЃЩњЛюЙЙГЩЕФетвЛЬѕЯпЫїЃЌЮЇШЦдквЛИіВЂВЛДѓШІзгжаЁЃдкЁАЙцбЕгыГЭЗЃЁБЕФПеМфжаЃЌЮвУЧПДЕНСЫГЙЕзЕФБЉСІЁЃЖјдкЦНЪгЕФШеГЃЩњЛюЪЕМљРяЃЌЫќУЧЪЧЁАЖрбљЕФЁЂЕжжЦЕФЁЂНЦЛЋЕФвдМАжДожЕФЁЊЁЊЫќУЧЬгЭбСЫЙцбЕЕФПижЦЃЌШЛЖјвВВЂВЛвђДЫОЭЭъШЋДІгкЙцбЕЕФЪЦСІЗЖЮЇжЎЭтЁБЁЃБГОАжадјОЕФЪЏПтУХРяХЊе§ЪЧЗжЮіетжжЪЕМљЕФзюМбГЁЫљЃЌРяХЊПеМфздЩэОЭЪЧЁАШЋОАГЈЪгМргќЁБЕФвЛДІЫѕгАЁЊЁЊкфФАЕФжЇХЊжаЪЧОгзЁПеМфЃЌНЯПэЕФжїХЊдђЖдЭтГЈПЊЁЊЁЊДјгаАыЫНУмАыПЊЗХЕФаджЪЃЈетРяЕФСЊХХКЭГЈПЊЃЌЪЧгЩГЧЪаЛЏКЭЁААыжГУёЁБЕФвЛЗНДјРДЕФЃЉЁЃОЭЪЧдкетРяЃЌСНЮЛАЂвЬМсЪизХздМКЕФЁАСьЕиЁБЃЌжБАзЕиЦчЪгЭтРДепВЂвЊЧѓЁАУЅСїЁБЭГЭГЧЙБаЁЊЁЊЫ§УЧВЂВЛЁАДІгкЙцбЕЕФЪЕСІЗЖЮЇжЎЭтЁБЁЃвВЪЧдкетРяЃЌЫ§УЧПЊЗЂзХШеГЃЩњЛюЪЕМљЕФеНЪѕЃЌУцЖдЃЈЯѓеїзХГЈПЊЕФЃЉОЕЭЗНВЫ§УЧЕФЫНЗПЛАЃКЫ§УЧБЇдЙМвЮёРЭЖЏКЭЛщвіЩњЛюЃЌЫ§УЧЫпЫЕздМКЕФЩэЬхКЭЧщгћЃЌЫ§УЧгЧТЧЩњЛюЛЗОГЕФОчСвБфЛЏЕЋуПуНзХМДНЋЕНРДЕФзЊБфЁЃвЛБпжЏзХШоЯпЃЌЫ§УЧЩѕжСЮЊЗРЗЖадБЉСІЯыКУСЫЖдВпЃКдкПуЖЕРязМБИзХвўУиЕФРћЦїЁЃ
ЛЙгаЙбИОЗыАЂвЬЃЌЫ§ОРНсгкЪРЫзЕФЙцЗЖЃЌЕЋОРњжкШЫЕФШАЫЕЛЙЪЧУЛгаКЭЭѕНЬЪкНсЛщЃЌбЁдёМЬајСЕАЎЩњЛюЃЈетаЉЖМдкЮовтжаЯћНтСЫДэЮѓЗЂЩњЪБГТе§ЛЊЕФЗпХЃЉЁЃЗыАЂвЬАЎГЊИшАЎЬјЮшЃЌКЭОлВЭЭЌзРДѓЪхГЊГіЕФгЂЮФИшЧњОЊбоЫФзљЃЌДѓЪхЫЕЃЌЮФэuЕФЪБКђдкМвРявВвЊГЊЃЌЦяГЕЩЯАрЕФЪБКђвВЧсЧсГЊЁЊЁЊЁАЭќСЫИшДЪетЖрФбЙ§ЁБДЫЪБГЩЮЊвЛОфЗДПЙЕФаћбдЁЃ
ЁАШеГЃЁБЕФЗДПЙадКЭДДдьаддкжаЙња№ЪТжагШЦфЫЕЕУЭЈЃЌЦфдкПеМфжаЫљЖдгІЕФЪаОЎаоДЧбЇЃЌгУКСЮоМЩЛфЕФаІЯћНтКЭДлИФзХЕБЯТЁЃПЩВЛвЊЮѓвдЮЊЗыАЂвЬКЭгбШЫДѓЪхЕФИшЩљжЛЪЧЁАЖЋЗНАЭРшЁБЕФВабЊЁЃЩдзївЛИіПМЙХОЭЛсЗЂЯжNat King ColeдГЊЕФЁЖMona LisaЁЗКЭЁЖToo YoungЁЗЪЧ1950ФъДњЪЧааЧњН№ЧњЃЌвВОЭЪЧЫЕЫќУЧдкжаЙњБЛДЋГЊжЛПЩФмЪЧдкЁАЗЧГЃЁБЕФ49ФъжЎКѓЁЃетВЛЪЧЪВУДЁАРЯПЫРеЁБЕФДЋЫЕЃЌвВВЛЪЧЕлЙњжГУёЪБЦкВМЖћЧЧбЧОЋЩёвХжщЃЌЖјЪЧецЪЕЕФЖМЪаШеГЃЩњЛюЃЌЁЖЪХЁЗжаЕФЩЯКЃШчДЫецЪЕЃЌЫќЕФецЪЕАќКЌзХДжБЩКЭВЛНВЕРРэЁЃ
жГУёГЧЪагыГЧЪажГУё
етвЛЧњНсЪјдк1997ФъЃЌЫјЖЈдкСэвЛИіСьЕМШЫЪХШЅЕФЪБПЬЃЌОЙ§ВЛЖЯЕиЙцбЕгывХЭќЃЌНёЬьЮвУЧдНРДдНОЊвьгкЦСФЛЩЯЕФЫНЗПЛАКЭСїааЧњЃЌЩЯКЃБфГЩСЫШЫУЧЯАвдЮЊГЃЕФИпЖЫДѓЦјЩЯЕЕДЮЕФТНМвзьЩСвЋОАЙлЁЃдкзЪБОЕФМЦЫуЯТЃЌРЯОЩЕФГЧЪаЁЂРЯШЅЕФШЫЃЌУЛгаЪмЙ§ИпЕШНЬг§ЃЌВЛФмзЅзЁЪаГЁЛњЛсЕФШЫЃЌбИЫйБЛГЧЪаЯѓеїадЕиЧаГ§ЁЃ
ЁАПЊЗХЁБжиаТКмСюаэЖрШЫгжРжЙлЦ№РДЃЌздгЩЫЦКѕзмгавЛЬьЛсЫцжЎЖјРДЁЃШЛЖје§ШчЪЏПтУХРяХЊЕФЯћЪЇЁЊЁЊЮоТлЪЧВ№Г§ЛЙЪЧаТЬьЕиЁЂЗсЪЂРяАуЕФЭЕСКЛЛжљЁЊЁЊжеНсСЫАыЫНУмАыПЊЗХадЕФеХСІЃЌШеГЃЩњЛюЪЕМљЕФеѓЕиОЭБЛДнЛйЃЌШЁЖјДњжЎПЊЪМЕФЪЧдзгЛЏИіЬхЕФжаВњНзМЖаТЙЪЪТЁЃЮєШежГУёепЪЦСІЕФДѓЦѓвЕЁЂПчЙњЙЋЫОгжгаЛњЛсНјШыетзљГЧЪажЎжаЃЌдкзпЯђОМУжїШЈСшМнеўжЮжїШЈЕФаТЁАЕлЙњЁБЪБДњжаЃЌЫћУЧгжБЛЧПДѓЕФЭГжЮепРћгУЃЌЮЊКѓепеѕЕУОМУАдШЈЁЃдкетСНЗНКЯФБЕФПеМфЙцЛЎжаЃЌИіЬхЕФМлжЕВЛЕЋВЛБЛз№жиЃЌЩѕжСШЫУЧРЭЖЏЪЃгрЕФЯћЗбКЭанЯаЪБМфЛЙвЊМЬајБЛАўЯїЁЃжБЕННёЬьЃЌЕиВњЩЬКЭеўИЎШдзЮзЮВЛОыЕидйЩњВњГЧЪааЮЯѓРДЬсЩ§здМКЕФЮФЛЏзЪБОЃЌЪВУДЁАЙњМЪЛЏДѓЖМЪаЁБРВЃЌЁАКЃФЩАйДЈЃЌДѓЦјЧЋКЭЁБРВЃЌЁАДгЪЏПтУХЕНЬьАВУХЁБРВЃЌЛЙгаДђдь ЁАОВАВЧјЕФаТЬьЕиЁБЁЂЁАКчПкЧјЕФаТЬьЕиЁБЕШЕШЕШЕШЁЃЮвУЧЖМЬхЛсЕУЕНЃЌОйАьИїжжЙњМЪЛсеЙЖдШеГЃЩњЛюЕФМљЬЄЃЌШЛЖјЮЊСЫБъЪЖздМКЕФИпЙѓЪаУёЩэЗнЁЂЮЊСЫЯћЗбетжжЁАЙ§ЖШецЪЕЁБЕФЮФЛЏЃЌЮвУЧгжВЛЕУВЛаРШЛЕиНгЪмЁЃЮвУЧЫЦКѕЭќМЧСЫШеГЃЩњЛюЪЕМљЃЌЭќМЧСЫдкЖМЪааазпжаЕФЛьучКЭОЊЦцЁЃ
вбОЙЬЖЈЯТРДЕФГЧЪаЩњЛюЗНЪНКЭвтЪЖаЮЬЌЁЊЁЊЪаУёЖдЩшМЦКЭЦЗжЪгаЦЋКУЃЌЯВЛЖНрОЛгыжШађЁЊЁЊДгГЧЪажааФвЛУцЯђНМЧјжГУёЃЌвЛУцЯђГЧЪажааФФкВагрЕФОЩОгжГУёЁЃЧюШЫЁЂЮоМвПЩЙщепЁЂЭтРДЮёЙЄепЁЂЮоСІАсГіОЩЧјЕФФъГЄепГЩЮЊГЧЪажГУёжаЕФЖўЕШЙЋУёЁЃетИівВБЛГЦжЎЮЊЪПЩ№ЛЏЕФЙ§ГЬжаЃЌЮвУЧОмОјСЫЪаОЎЕФаоДЧВЂНгЪмСЫЗжСбЁЃвЛаЉЪЏПтУХвђЦфПЩБЛРћгУЕФЕиВњКЭЮФЛЏЗћКХМлжЕЃЌГЩЮЊОіВЛИќИФЕФБЃЛЄЧјЛђПЊЗЂЩЬблжаЕФЯутЩтЩЁЃИќЖрЕФЪЏПтУХдђБфГЩЗЯацЁЂГЧжаДхЁЃвЛаЉШЫзїЮЊШЫВХв§НјВЂБЛзМаэЙКжУЗПВњЃЌСэвЛаЉШЫдђЯрЗДЭЈЙ§ЁАЮхЮЅЫФБиЁБЕШЕШећжЮжБНгАўЖсНјШыГЧЪаПеМфЕФШЈРћЁЃЩЬГЁетИіРћЮЌЬЙГЩЮЊЮвУЧзЄзуКЭЭЃСєЕФЕиЗНЃЌЬсЙЉбЯЫрЬжТлЛђЪЧПЩвдздгЩанэЌЕФЙЋЙВПеМфБЛЛФЗЯФЫжСФЈГ§ЁЃНЋШЫУёЮоШЈВЮгыЕФГЧЪаеНТдХзжЎФдКѓЃЌЮЊСЫДюЩЯЁАЩ§жЕЁБЕФПьГЕЃЌзюжеЮвУЧЦкаэГЩЮЊвЛзљЁАЗЧШЫЁБГЧЪажаЕФЪаУёЁЃЁАщыдсЪНЁБЕФЭГвЛЕъеаФжСЫаІЛАЃЌЮвУЧШДВЛвЊКіЪгвЛИіЪТЪЕЃКжЮРэепКЭзЈвЕШЫЪПНсУЫКѓЭЌбљПЩвдШУОЋаФЩшМЦЕФЕъеаБфЕУКУПДЁЃетФбЕРОЭВЛДцдкЭЌбљЕФЁАжГУёЁБСІСПТ№ЃП
ЖМЪаЕФБОжЪЃЌЪЧПеМфжаИіЬхЕФЁАОлМЏЁБЃЌЫљЮННјШыЖМЪаЕФШЈРћЃЌОЭЪЧетжжОлМЏЕФШЈРћЃЌЪЧОмОјБЛХХГіЕФШЈРћЁЃвЛЕЉГЧЪаЙцЛЎКЭПеМфЩшМЦДђзХЁАРњЪЗЮФЛЏМлжЕЁБЁЂЁАећжЮИќаТЁБЕФРэгЩЗДЖдОлМЏЕФШЈРћЃЌЖдШеГЃЩњЛюПеМфРДЫЕЖМЪЧвЛДЮгжвЛДЮЕФЛйУ№ЁЃ
ЪЧЕФЃЌИќВЛвЊЫЕБЛЭэЦкзЪБОжївхОЋзМПижЦЕФШЫЕФЪБМфЃЌЮвУЧЛђаэЮоЗЈеѕЭбЗЧШЫГЧЪаЦњЖљЕФУќдЫЁЃЕЋвВЮоЗЈАкЭбГіТєздЩэЕФНЙТЧЃЌвђДЫЃЌвВОЭБШШЮКЮЪБКђЖМашвЊевЛиШеГЃЩњЛюЪЕМљетИіеНГЁЁЊЁЊдкФЧРяЮвУЧШддкзізХЙигкГЧЪаЕФУЮЃЌЛђаэЪЧвЛДЮЬИЬьЁЂЛђаэЪЧвЛДЮЙлгАЁЂЛђаэЪЧвЛДЮЩЂВНЁЃЛиПДдкНжЕРжаСєЯТЕФНХВНЃЌФФХТ20ФъРДЮэіВЪМжеС§ежзХГЧЪаЃЌЕЋШЫУЧЛЙЪЧдкЩњЛюжаГаЪмСЫГЧЪаПеМфжаЕФЕуЕуЕЮЕЮЃЌВЂЧвНЋМЬајдкЗьЯЖжаЩњЛюЯТШЅЁЃжЛвЊСбЯЖЛЙдкЃЌОЭгаЛњЛсжиаТЁАОлМЏЁБЃЌНЈдьаТЕФЖМЪаЁЃФФХТетзљГЧЛЙЩаЮДгаНЈжўЮяЃЌжЛгаМЧвфЁЂЯыЗЈЁЂОЋЩёЁЂФбвдзНУўЕФЦјЮЖЫљЙЙГЩЕФФЃК§НжЕРЃЌШдгаЛњЛсЭЈЙ§УПвЛИіНХВННЋЫќУЧБржЏНјЯжЪЕжЎжаЁЃ
Copyright © 2024-2025 All Right Reserved.
GMT+8, 2026-1-19 21:32 , Processed in 0.020402 second(s), 19 queries , Gzip On.
免责声明:本站仅为用户之间信息交流之媒介,所有内容均来源于网络或用户投稿,本站服务器不储存任何音视频文件,所有内容包含图片的版权均归原作者所有。站内下载链接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,请于24小时内自觉删除,若用户非法收藏、传播或将资源用于其他商业用途,均与本站无关,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使用者自行承担。如本站点所发布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,请第一时间联系管理员317379335@qq.com,我们将及时予以删除,并致以歉意!

联系管理员